唐小兵教授

唐小兵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ril 2024
唐小兵,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从1991年至2008年间,曾先后任教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德)、芝加哥大学及南加州大学。2008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Helmut F. Stern现代中国研究教授及比较文学讲座教授。2019年9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至今。
其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视觉文化、艺术史、声音研究及文化政治,曾出版多本著作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英文著作包括:《全球空间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论述:梁启超历史思想论》(1996),《中国现代:英雄的与日常的》(2000),《中国先锋的起源:现代木刻运动》(2008),《当代中国视觉文化:范式与转换》(2015)等。中文书籍包括:译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1986),其主编的论文集《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以及《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2018)。

演讲题目:
经典重读:鲁迅的故乡和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时间:
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
下午3时至下午4时30分
地点:
报业中心礼堂 (News Centre Auditorium)
1000 Toa Payoh North, News Centre, Singapore 318994
摘要:
鲁迅192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乡》有鲜明的自传成分,同时也是一篇关于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经典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范式意义的作品。唐小兵教授将对这个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揭示叙述者复杂的心路历程和作品的魅力所在。
演讲纪要
由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主办的“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于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下午3时至4时30分,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出席者209人,现场反响热烈。
此次演讲题为“经典重读:鲁迅的《故乡》和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由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华裔馆馆长游俊豪副教授致开幕词并担任主持。游教授首先欢迎唐小兵教授的到来,并由衷感谢联办机构和出席者的支持,同时介绍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设立及其演讲活动,接着介绍了演讲者——唐小兵教授的研究领域、出版著作及其学术影响力。
唐教授的演讲主要聚焦于对《故乡》的文本细读,并探讨鲁迅这篇极具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叙述者复杂的心路历程与其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
唐教授首先简短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创作背景、人生经历和《故乡》的剧情。唐教授指出,《故乡》是根据鲁迅最后一次回到绍兴老家的经历所写,同时也是在回应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对于“故乡”的一种核心叙事。唐教授认为,“故乡”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自我认同和定位,是“低头思故乡”的思念,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中“我”的故事,是“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后的底色,是自我身份与记忆的代名词,是归属,也是根。
唐教授接着对小说的内容进行探讨。在小说中,叙述者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内心经历了从怀旧、失落到深刻反思的情感转变。这种情感转变与陶渊明诗中对故乡田园生活的理想化描绘形成了鲜明对比。唐教授认为,后者表现出对回乡的“解甲归田”的情绪,而前者似乎对回到故乡持有一种“过客”的心态。唐教授通过叙述者在文本中使用的“回到故乡去”而不是“回到故乡来”来进行论证。他指出,“去”字代表着叙述者如今的栖息地远离故乡,同时叙述者也只是回“去”暂居办事,很快便将再度离“去”。唐教授强调,与陶渊明对归隐生活向往的描写不同,鲁迅笔下的叙述者在重返故乡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这包括对过去纯真时代的追怀,以及对当下现实的失望。叙述者在面对故乡的巨变时,深刻体会到了时间流逝带来的无可逆转的变化。
唐教授进而剖析叙述者对“故乡”记忆的多层面性。他强调,鲁迅透过叙述者的视角展示了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揭示了人们对于理想化过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性认知。在小说中,“故乡”被描绘成了儿时的记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这些记忆逐渐被遗忘。唐教授指出,“故乡”是由儿时记忆构成的,而儿时记忆具有与成人世界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当叙述者在成人世界中重新唤起对“故乡”的记忆时,并未感受到应有的熟悉感,反而带上了神秘色彩。因此,“故乡”在叙述者心中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家园象征。这种深入的解读不仅丰富了读者对《故乡》的理解,也引发了人们对记忆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
在探讨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观点时,唐教授强调了人们往外地定居并将生活放在首位的趋势,而这使得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化。唐教授认为:《故乡》中的叙事者虽然对回乡之行感到失望,但却将希望寄托在侄儿身上,期望他能够比(叙事者)自己更有所收获。唐教授指出,鲁迅对“故乡”的描写呼应了中国千年来的“故乡情怀”,尽管鲁迅的精神家园并非真正的“故乡”,但他仍然期待着下一代能够重新找回这种情感纽带。这一观点不仅深刻解读了《故乡》,也呼应了现代人对于精神归属的复杂追求。
唐教授在演讲中不仅对鲁迅《故乡》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为当代人对精神归属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视角。唐教授指出,《故乡》揭示了人们面对变迁时的共同情感和普遍困惑,同时表达了人们对下一代能够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分析不仅可以启发读者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也为追寻精神归属的现代人提供新的启示。
在问答环节中,唐教授进一步补充道,任何一部作品只要仔细品味,都能从中读出深刻的意义。面对经典文本,读者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而不是随意用现代眼光去批判。当听众提问关于鲁迅的人生轨迹,特别是他离开故乡的经历对他人生的意义时,唐教授回答说,对于鲁迅而言,“故乡”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然而,从重要性来看,《故乡》标志着他写作生涯中关于农民题材的开端,同时也为他后来创作《阿Q正传》奠定了基础。
唐教授总结道,“故乡”是一个人出生或成长的地方,具有深厚的文化和记忆连结,“精神家园”则超越了地理位置,指的是一个人在思想或情感上找到归属感的场所。虽然“故乡”提供了根基,但“精神家园”是由个人选择和创造的,是心灵的栖息地,且对于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至关重要。
至此,2024年4月“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英文演讲

演讲题目:
现代中国的新声音:从有声电影到民众歌咏
时间:
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
下午4时至下午5时30分
地点:
南洋理工大学福建会馆大楼会议室(SHHK-05-57)
48 Nanyang Avenue, Singapore 639818
摘要:
193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民众歌咏,有众多历史条件和因素的推动,也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新的声音技术(比如收音机和有声电影),新的发声歌唱的主体,以及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共同促进了民众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传播,并由此而催生了一种新的 声音文化。1935年在上海首映的一部有声电影的主题歌,是这种新声音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迅速流传和经久不衰的号召力生动地说明了新声音文化的历史意义。
报名链接:
https://wis.ntu.edu.sg/pls/webexe88/REGISTER_NTU.REGISTER?EVENT_ID=OA24040117522219
演讲纪要
4月26日(星期五)下午4时至5时30分,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场“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在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福建会馆大楼五楼会议室举行。此次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陆镜光教授主持。陆教授致辞欢迎唐小兵教授的到来,并由衷感谢联办机构和出席者的支持。他介绍了唐教授的研究领域、出版著作及其学术影响力,同时介绍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设立及其演讲活动。
唐小兵教授的讲题为“现代中国的新声音:从有声电影到民众歌咏”,内容概括为:1930年代的新声音技术在当时的上海催生了一种新的声音文化。唐教授认为,1930代开始发展的声音技术,如收音机和有声电影,与中国当时的强烈民族危机感,是推动民众歌咏的蓬勃发展和传播的主要推手。
唐教授首先说明,“现代中国”指的是中国处于清末民初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时期。唐教授认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脱离了千年以来的帝制体系而转型成为民国的政治体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从“旧中国”的废墟中重建出一个“新中国”。一个崭新的“中国文化”便是组成答案的核心部分,其中从1915年至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为之后的许多运动提供了范式。
193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新声音文化便是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新文化”。唐教授认为,这种“新文化”的诞生是因科技创新、战争危机和大众文化的碰撞而生的。唐教授以作曲家聂耳的歌为例子,探讨了收音机的普及使得音乐能够超越之前的空间限制,面及更广泛的听众。这种即时性的传播媒介让民众能够更快速地接触到各种流行歌曲,从而提升了社会对音乐的整体兴趣和参与度。以聂耳为例,其谱写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先经由电台传播,才介绍给普罗大众的。
与此同时,有声电影的出现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声音文化。特别是戏里的歌曲,让电影的故事不仅仅是能够“听得见”,“更能够看得见”,因为歌曲的元素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情感更加丰富。唐教授指出,一个人的声音是孤单、弱小的,而如聂耳创作的被大众传唱的歌曲,却可以创造出一种民族集体声音。聂耳在1935年的有声电影《风云儿女》中所作的主题曲,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曲。
不幸的是,聂耳在1935年便去世了,但他的精神和音乐遗产被刘良模等后来者所继承。刘良模不仅将聂耳的音乐推向了新的高峰,还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歌咏的风潮。唐教授指出,“民众歌咏”并不是传统中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它更多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唱诗班,而刘良模便是主要推动者。自1934年开始,刘良模便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同年,他在上海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到了1935年2月,拥有300余名会员的民众歌咏会正式成立。自此,“民众歌咏”慢慢散播到中国各地。1941年,刘良模在美国结识了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两人合作录制了一张专辑《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收入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中国流行歌曲。刘良模的努力使得音乐成为了连接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域的桥梁,使歌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共同的身份与声音。
唐教授总结道:1930年代的声音技术革新,特别是在上海,不仅催生了一种新的声音文化,而且推动了中国民众歌咏的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一种声音,使得全世界都听得见“中国的怒吼”。其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还在塑造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和文化身份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并持续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许多表演形式。
在问答环节,听众就五四时期因赵元任与刘半农所兴起在学校教授音乐课、早期的歌曲并非为“民众歌咏”所写、以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影响等相关课题提出问题,唐小兵教授都一一做出解答。至此,这场精彩的演讲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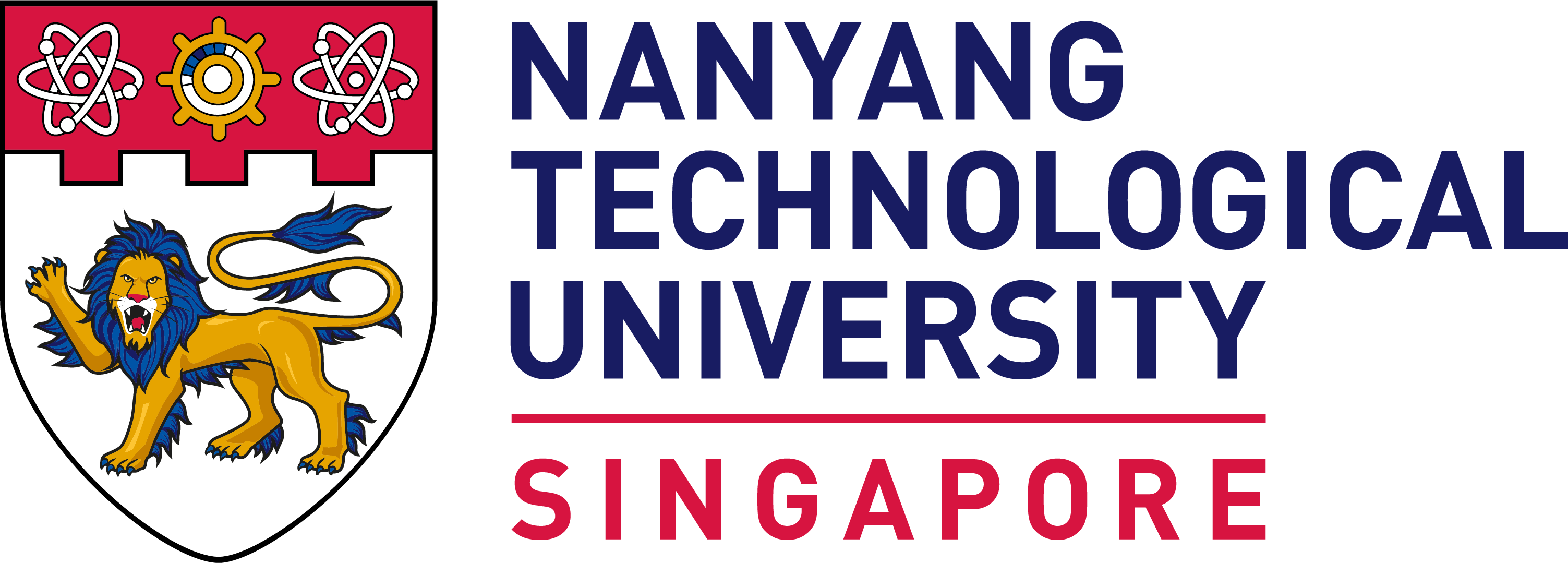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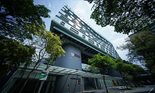

/enri-thumbnails/careeropportunities1f0caf1c-a12d-479c-be7c-3c04e085c617.tmb-mega-menu.jpg?Culture=en&sfvrsn=d7261e3b_1)

/cradle-thumbnails/research-capabilities1516d0ba63aa44f0b4ee77a8c05263b2.tmb-mega-menu.jpg?Culture=en&sfvrsn=1bc94f8_1)
